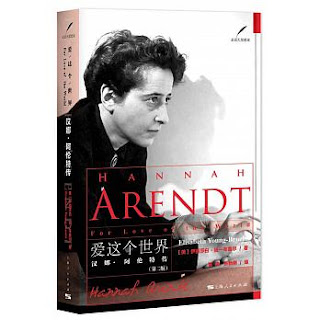2018年6月18日
//上海的小書店,很多是誠品+台灣獨立書店的綜合版,逛起來格外有台灣的fu!
但翻譯書的類型之廣,題材選擇之多樣,跨國譯介之多文化,台灣恐怕早就瞠乎其後了!(這無關乎面子問題,而純粹是市場吞吐量的現實。)
我坐在長寧區「幸福里」的小文創區裡,一家集潮牌設計與書店的空間裡,挑了幾本史考特.費茲傑羅的小說,艾倫.金斯堡的詩全集,當大陸出版界也展現出不熱門書籍的翻譯企圖時,台灣是該當心而戒慎恐懼的想想:我們該怎麼辦?//
//進入書店後走不了多少步,便見到一列數十本外文詩集中譯本,這是我第一次在書店最當眼處見到大量詩集,可謂不同凡響!這裏的書夠多,質素也高,尤其是文學和歷史書(可惜余英時的書被禁了),文青到這裏消磨時間定必愉快;事實上,當日在店中所見大多是年青人。書店內人很多,但一點也不嘈吵,幾乎人人都在低頭看書或在書架上找書。……
書店內有幾張大枱和很多座椅,也有沙發和長椅,簡直是鼓勵顧客打書釘,而看來是在打書釘的人當真不少。店內任人飲食,但不見地上有垃圾,可見飲食者很自律。//
在我看來,兩位先生所講的應該都是事實,沒什麼好爭論的。中國翻譯書類型、題材和語種之廣泛多樣,多年前應該就已經超過台灣了。市場夠大確實有許多好處,例如小眾的書比較容易找到夠多讀者支持,得以出版發行:同樣的書在台灣要賣三千本可能很困難,但在中國或許並不難。一家出版社如果以出版相對冷門的書為主,它當然希望自己的市場是中國那種規模,而不是僅限於台灣和香港。
但我們談翻譯書,不能不談翻譯素質。多年前,香港的林行止先生在其專欄曾提及中國現在翻譯出版相當活躍,不少有犯禁嫌疑的名著都獲准出版,但他冷冷地說:中國政府准許這些譯作出版,可能是因為很多譯文莫名其妙,讀者都看不懂。梁文道寫過一篇〈翻譯的態度與常識〉,談到他讀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發現的翻譯問題,相當有趣。于連那本書夠冷門,台灣和香港都沒出中譯本;對想看該書但無法看原文的讀者來說,中國出中譯版本是好事,但譯成那樣,大概會有人覺得不出中譯比較好。
講到這裡,難免又要談這問題:台灣出版的翻譯書,翻譯品質有顯著優於中國嗎?這問題必須認真做過研究才能真正回答,個人只能憑自己有限的經驗提出未必準確的看法。我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不代表台灣出版的翻譯書品質普遍優秀。歷年來對台灣出版業翻譯品質的批評也不少,關心的人自然知道。台灣翻譯出版業面對的結構問題除了市場規模相對有限外,就是投入書籍翻譯的人才不足(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市場規模不足限制書籍翻譯的報酬,進而限制人才供給)。中國的市場規模較大,但書籍翻譯的報酬也普遍不佳,因此恐怕也不容易解決書籍翻譯人才不足的問題。
談中國的翻譯出版,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中國是嚴厲管制出版的國家,書籍即使能出版,內容也往往因為出版社自我審查或政府的審查而刪除任何可能犯禁的內容。數年前就有中國譯者在網路上公開表示,他翻譯 Milton Friedman夫婦的 Free to Choose,許多譯文被出版社刪掉了;他因此建議中國讀者盡可能讀原著,因為「中國大陸目前出版的譯著,基本上都存在刪減的現象,原因就是意識形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