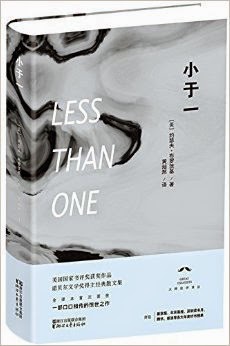2015年2月18日
As failures go, attempting to recall the
past is like trying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Both make one feel like a
baby clutching at a basketball: one's palms keep sliding
off.
黃燦然譯文:「跟一般失敗比較,試圖回憶過去就像試圖把握存在的意義。兩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嬰兒在抓籃球:手掌不斷滑走。」
台灣譯者張華先生在我的網誌留言,提出他的譯法:「回想過去和思考存在的意義,這兩事都像嬰兒抱藍球一樣,想抓卻抓不住,往往注定失敗。」
我在日前文章中提到,我不明白黃燦然為何將「As failures
go」譯成「跟一般失敗比較」,鍾漢清先生在我臉書頁面留言,說「as xx go」的意思是Compared to the average or typical one
of the specified kind,例如As castles go it is small and
old。他這麼一說,我馬上便知道黃燦然為什麼會這麼譯。
因此,黃燦然將「As failures
go」譯為「跟一般失敗比較」,意思確實沒錯,但這不代表他譯得好,因為無論如何,「跟一般失敗比較,試圖回憶過去就像試圖把握存在的意義」這句話是很難理解的。張華先生將兩句原文併譯,我認為是高明的做法,但如果要單譯第一句,我應該會這麼譯:「就失敗而言,試圖回憶過去就像試圖掌握存在的意義。」
讀者或許會質疑,我這麼譯並沒有嚴格遵照「as xx go」的辭典解釋,是否扭曲了原文的意思?我只能說,如果你像黃燦然那樣直譯,讀者是幾乎無法理解作者想說什麼的。有時候作者的用詞並不會嚴格遵照辭典所載的正統用法,怎麼譯還是必須看context。就此例而言,如果我們將原文頭兩句放在一起看,不難看出作者要表達的意思其實很清楚,並沒有什麼隱藏的深意可言,所以這裡將兩句併譯確實應該是較好的做法。我會這麼譯:「試圖回憶過去就像試圖掌握存在的意義,兩者均使人覺得自己像嬰兒嘗試抓住籃球:手掌不斷滑走,注定徒勞無功。」
謝孟宗先生在我臉書頁面提到,黃燦然信奉「直譯觀」,所以他會這麼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套路數確實不高明。單從此例看來,的確是這樣。我無意論斷黃燦然的翻譯品質,因為一個人的翻譯品質不能單看一兩句翻譯斷定,而《小於一》這本書原文第一篇我看不下去,覺得很不好理解,所以也就不想去看黃燦然譯得如何了。
不過,我個人認為翻譯常常是不能直譯的,因為如果你懂原文,你看原文可以理解,但你直譯出來讀者很可能無法理解。我舉個例子,Martin Wolf 在 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的引言中有這麼一句:「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Even the
quite recent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at is certainly true of the views of
leading policymakers.」如果直譯,大概是這樣:「過去是外國。即使是最近的過去也是外國。政策制定者的觀點肯定是這樣。」我相信中文讀者絕大多數會覺得這樣的譯文很費解。我會這麼譯:「昔日如異邦。往事即使才過去不久,放在今天仍往往顯得怪異。政經決策者的觀點無疑是這樣。」
我不敢說我這種翻譯方法是最好的,但我認為在很多情況下,譯意不譯字是較好的做法,有時甚至是必要──這是為了給讀者通順、易懂而且意思正確的譯文。我真的不認為將原文的字詞直接譯過來,就是忠實的翻譯。我覺得那往往只是譯者懶惰罷了。我並不是主張完全不理會原文用什麼字詞:如果直譯可以得出通順、易懂而且意思正確的譯文,我通常是會直譯的。
黃燦然在《明報》那篇訪問中提到:「我可以寫出一句百多字的句子來,但可能連自己都讀不來,只要我自己可以接受,我便直譯。我相信讀者比譯者聰明,既然我自己讀得懂,那麼讀者就一定能懂。你總不能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那是不負責任。」張華先生對此有自己的看法,我覺值得放在這裡供讀者參考:
一、黃燦然比擬不當,把一般智商與特定語言能力混為一談。
二、黃燦然對讀者其實是明褒暗貶,讀得懂譯文是聰明,讀不懂就是白癡。譯者有原文作比對,譯者讀得懂自己的翻譯,往往是有原文對照,加上譯者對原文文字與文化背景有深入理解的緣故,有人主張要把譯文擺一段時間再讀,便是避免原文印象的殘留影響。
三、黃燦然甚為自負,認為自已的翻譯一定正確無誤,讀不懂是讀者的問題。其實翻譯經常出錯,抱括原文看不懂、原文讀不透、翻譯筆誤、譯筆生硬、詞不達意等。讀不懂的句子,往往是譯文出了問題,不適讀者笨,像「跟一般失敗比較,試圖回憶過去就像試圖把握存在的意義」一句。譯者也有「當局者迷」的時候,有些翻譯上的錯誤,讀者一看就出來,譯者自己卻始終沒發現。
五、「把讀者想像成一個白癡」一語,還是把把讀者的智商與語言能力混為一談。譯者要注意的,是讓不懂原文的讀者看得懂,而不是為了貼近原文而犧牲了理解度。讀者看不懂或是讀得很幸苦,不是讀者白癡,往往是譯者沒把翻譯做好。
張華先生曾在〈翻譯半生緣〉一文中敘述他的翻譯經歷,值得一讀。